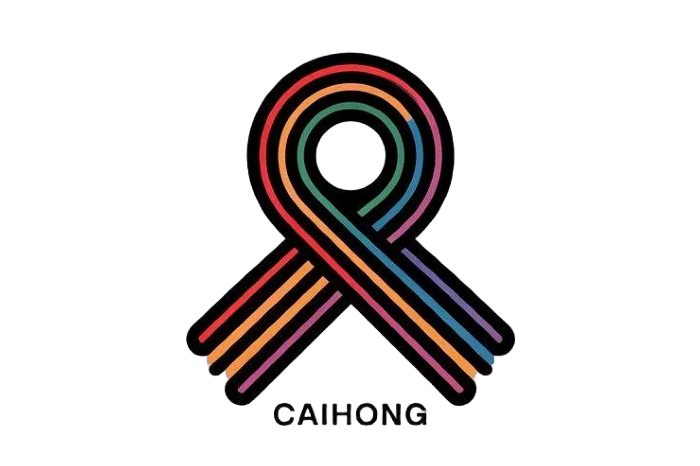同性恋孤儿:我不用担心结婚这个问题

2021年8月,晚上六点多,躺在只有四十平老房子里的龚强听到手机短短的震动,他一骨碌爬起来、伸长胳膊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可看到微信的一刹那,他又瘫在了床上。
微信是龚强的母亲发来的,内容和这个月之前发来的几条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发工资了吗?”龚强哭笑不得,心里堵着。母亲每个月都会来要钱。“只要不是几百块,给她一千两千三千都不挑。”
但今日的龚强已非从前,“妈,我都快失业了。你还一个劲儿地管我要钱啊!”龚强发完这条语音,又颓在床上摊开身体。他是一名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自从国家实施“双减”政策后,已经快一个月没上班了,平时的他,只能靠家教过活。
最后一万块钱
8月末的一天,龚强冲进地铁站时天空还在下着大雨。一个小时后,他从城市另一边的地铁站出来时,天空已经转阴。龚强顾不得鞋子和裤脚浸湿,在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向做家教的小区奋力蹬去。
到了高层楼下,按响门铃,那端传来女主人的声音,“你在楼下没看见我家孩子吗?”龚强一愣,“不是约了这个时间家教?孩子怎么能在楼下?”女主人听起来也很无奈,“他说不愿意家教,就跑出去了。我也拦不住。”“那你给孩子打个电话吧!”龚强的语气有点生硬,他真的不高兴,“我等你一会。”
几分钟后,女主人打过来,“孩子不接电话。老师,真抱歉,让你白跑一趟。”龚强心里老大不愿意,今天这五百块钱又跟他一起泡汤了。
龚强的家教价格在高三年级中算低的。他多半靠熟人介绍。换做两个多月前,他恐怕都没时间接这样路途遥远的家教,“周末两天、平时晚上六点到十点,排得满满的。讲一个小时,只能休息十分钟。到了周一白天,真是嗓子疼得一句话都不想说。”而现在,一天能有一次家教已经算“爆单”。
龚强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脱掉湿袜子,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你还没发工资啊?”“你不是找了份超市的工作吗?还这么缺钱?”龚强有些不耐烦。“我可干不了这个活儿。”母亲在电话里的语气让龚强甚至想象得出这个年近六十的女人眼睛一眯、嘴一咧的表情。
“在超市干活不比伺候家里那几亩地轻松?”龚强继续说。“时间长、不让休息。天天被使唤。”母亲在声音上压过龚强,“不说这些。你这个月到底发工资没?以前这个日子都发了的。”龚强气得语速更快,“我都快失业了,你咋不问问我咋活下去?就知道要钱。”
龚强的母亲面对儿子的指责总是临危不乱,“你就给别人讲讲课、动动嘴,几百块就到手了。你看我和你爸,像你这个岁数时,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老了这疼那疼。哪有你赚钱这么轻松。”龚强知道自己再说下去也是于事无补。他一边听着母亲喋喋不休,一边看了看微信余额,还有不到两万块钱。
“你月月管我要钱。就没想过管我姐要钱吗?”龚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对了,提到你姐,你还真要多给我一些钱。我打算这个月去你姐家帮她带孩子。你姐也不容易,嫁了个男人,好吃懒做。我不去看看都不放心,不知道她这日子怎么过……”
“行了,我最后给你一万,你以后别管我要钱了。你从大学就不管我。你再要钱,咱俩就断绝母子关系。”说完,龚强挂了电话。他转了一万块钱给母亲,母亲连一秒钟都没耽误,收了。剩下的九千多块钱中有六千是接下来半年的房租。而培训机构这个月一千五的底薪还没发。龚强感觉从心里到外的累,喘气都费劲的累。
“我不会朝鲜语族”
2019年,没有新冠疫情,也没有“双减”政策,龚强还有个男朋友。在他看来,那段日子虽然满是争吵,但他的身体至少有个温暖的去处。时间再往前推一些,2010年龚强读大二。母亲一个月给他五百块。这五百块不仅包括了生活费,还包括了学杂和住宿费。“根本不够用的。”龚强只能试着打工赚些钱。
“你是朝鲜族?”一家烧烤店的老板看了眼龚强的身份证,“你会说朝鲜族话不?我们这里几乎都是朝鲜族的。”龚强迟疑了一下,摇摇头,“我爸我妈和我姐都会,就我不会。”老板叹了口气,“太可惜了。看你人高马大的,应该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但不会朝鲜族话……”
从龚强记事起,父母在家里就对自己讲汉语,而跟姐姐讲朝鲜族语。其实龚强听多了,也会一点。有一次母亲听见龚强和姐姐用朝鲜族语对话,立刻把刚上小学的龚强打了一顿,边打边训,“谁让你学的!”父母一辈子干农活,手很有劲,龚强被堵在土炕一角,打得几乎昏过去。从那之后,龚强再也不敢表现出来自己会朝鲜族语了。
龚强读小学二年级时,母亲的腰忽然坏了。他只知道父亲带着母亲去了城里治病,一去就是半年多。那几个月里,龚强跟着姐姐,两人摸索着学会了煮饭、炒菜,在左邻右舍的指导下学会了下地除草、施肥和打药。
2011年,龚强看到校园里张贴着招聘兼职教师的广告。一节课六十块钱。他在心里迅速算了一下,如果一天两节课,一个月就可以到手三千多元。那他就不需要母亲“施舍”的那五百元了。更让龚强没想到的是,做了半年多小学补习班老师后,自己被安排到初中补习,课时费也涨了。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家长。那时还不确定自己喜欢男生多些还是女生多些的龚强,第一次跟了这位大叔。其实大叔的孩子不是龚强的学生。两人不过是打了个照面,龚强就电光火石般开了窍。等到在培训学校旁边的浴池再次偶遇后,他们对上号,约着去了旁边的酒店。龚强从此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一年后,龚强大学毕业,顺势就在这个培训学校入职,从初中部调入了高中部,收入丰厚了许多。可他还是偶尔想起2012年那个大叔给他的温暖身体,“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叔让我觉得温暖。连我妈都没给我这样的感觉。”
2015年底母亲再次摔伤。这一次伤得很重,需要置换人工软骨。一辈子务农的父母掏不出将近十万的手术费。那时已经出嫁的姐姐却主动跟龚强商量,“你看你姐夫也没工作,我也在家备孕,一直没上班。这个家里唯一有收入的就是你了。你还是男孩,要不你想想办法?”
龚强跟学校请了假,回了老家。到邻居和亲戚家一家一家地说好话、借钱、写借条,好不容易凑了六万多,再加上自己攒下的三万多,终于凑够了手术费。
母亲的手术是在省城做的。龚强没去照顾,连面都没露。姐姐去照顾了半个月。他不知道父母和姐姐在一起会用朝鲜族语议论些什么。以前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在家里,让龚强每一次都不太舒服。龚强清楚地记得,他从做了二十多年的老邻居家带着五千块钱走出来时,背后那一句“别看老龚家捡了个儿子,关键时刻还都靠这小子”。
这句话是用朝鲜族语说的。大家都以为龚强不会朝鲜族语。其实他听得懂。
“孤儿”
龚强已经有三年没回家过春节了。2020年是因为疫情。2018年和2019年是因为男友。龚强的男友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龚强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让他有“共鸣”的一点。他执拗地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孤儿”。
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问龚强要钱。男友曾劝龚强,“不如你直接问你的父母吧?”龚强不肯,他更不敢。他怕如果自己真的是父母捡来的孩子,接下来的日子,是和父母姐姐形同陌路,还是一如既往?无论哪一种,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忙碌的工作让龚强的业余时间变得很少。周末和公共假期都是最忙的时候,就连夜晚也是工作时间。但男朋友是做销售的,人活泼。夜里各种各样的“应酬”,让龚强眼花缭乱。一开始,龚强还会叮嘱“别喝多了”、“早点回来”。两个多月之后,两人开始就此发生无休止的争吵。
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太久,男友提出了分手。龚强特别不理解。和男友的分手让他无法在原来的住处继续生活。沿着地铁,他换到了距离学校四站地的另一侧。房租也比原来的要便宜。龚强自我安慰,“这样每个月可以多还一些之前借的钱了。”龚强在还钱这件事上,最初很有压力,他拼命攒钱,每个月可以攒下近五千。按照这样的速度,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还完之前的借款。可从2016年起,母亲每个月都会问他要钱。有时龚强忍不住发脾气不想给,母亲就安抚他,“我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还能有别的心眼嘛!将来要是攒下来钱,也都给你。”
龚强是从2017年开始再也不相信这些话的。那一年,龚强跟母亲商量,“我不能总是租房子啊!我怎么也要买个房子,也算是有个住处。哪怕小一点的二手房也可以啊!”电话那端的母亲正在跟左邻右舍的几个女人打麻将,心不在焉地说,“你这么大了,也该养家了。你每个月多给我一些,你想干嘛就干嘛,别的我不管。”龚强心里尖锐地痛了一下。挂电话前,母亲又急三火四地挤进来一句,“你最近多给我点吧,你姐打算要孩子了,我得多给她一些……”
“凭什么?”
“你不是还没对象嘛!你也没结婚,哪里就有那么多用钱的地方。”
母亲就没有心吗?龚强甚至后悔,当年的借条为什么是写了自己的名字?救谁的命,不就该写谁的名字嘛!
让龚强特别坚定自己是一个捡来的孩子的原因是父母从来都没有催他结过婚,“男孩要结婚,家里无论如何要出钱的。哪怕不买房子,聘礼总要给几万吧?”
从2015年给母亲治病后,父亲常年在外省打工。母亲去过外省一段时间,两个多月后就返回家,“那些活儿我都干不了。”而母亲口中的“那些活儿”也不过是一些后厨洗碗、超市理货。一辈子务农的母亲习惯了天大地大,不受管制。母亲催着姐姐结婚、然后又催着姐姐要孩子时,龚强还暗自庆幸,毕竟他喜欢男人。可如今想来,怎么母亲不催自己,反倒催姐姐?
一天,龚强结束了家教,路过城市里的室内冰场。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冬天,村子里的小孩扎堆玩一种叫做“滚冰”的游戏。其实就是在冰上划着冰车追逐打闹。因为谐音“滚病”、寓意把病都滚走,所以大人也愿意让孩子们去冻冰的河面玩。
一次,龚强跟姐姐一起从一个小陡坡上坐着冰车滑下来,半路磕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两人一起从裂缝的冰面掉进河里。因为是在河边,水不深,没啥危险。倒是衣服都湿透了。龚强不愿回家换衣服,怕被母亲骂。姐姐跑回家,足足过了快一个小时才出来叫龚强回家,“妈怕我感冒,给我洗了热水澡。现在让我叫你回家。”
龚强那时光顾着害怕。回到家,母亲让他用姐姐剩下的温水洗了洗,换了身衣服,并没有问他是不是冷了饿了。龚强一直以为是姐姐安抚了母亲。可如今,他电光火石一般: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担心过自己。
龚强不愿意想这些,可又忍不住。似乎每一条得到的信息都在指向那个答案。他甚至觉得,连自己这么努力工作的习惯,都跟母亲姐姐不一样。
2020年6月,龚强的手机响了,区号显示是老家的电话。他迟疑着接了,是五年前借钱给自己的一位老邻居的儿子,语气特别激动,“当年你妈病重,你过来管我们借钱,我们也借给你了。虽然就几千块钱,也不能一拖就好几年不还吧!我爸现在病了,钱是小事,你不还钱,老爷子心里憋气。”龚强虽然隔着电话,也被这段话数落得面红耳赤。
对方继续说,“我刚才去找你们家。一个人都没有。你妈是跟你在一起,还是跟你姐在一起?”龚强心里疑惑,“我好几年没回去了。我不知道我妈去哪里了。应该是跟我姐在一起吧?”对方也很无奈,“老龚家也就你这么一个人还算靠谱。你先把钱从微信上给我还过来吧!也让我爸别那么上火。”
龚强心里一动,“还钱没问题。我有个事想问大爷。你能帮我问一嘴?”对方听龚强说要问“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也是一愣,只能说“试试看”。龚强先把借的钱在微信上转了回去,又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对方才回信息说,“我爸说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他一个外人不好说,也不清楚。”
就在龚强反复品着这短短的一句话,打算回复“谢谢”时,对方忽然发了四个字,“你懂了吗?”龚强的背后慢慢渗出一层细腻的汗。
2021年9月,龚强又接到了母亲的“催款”信息。这一次他非常愤怒地拨了电话回去,“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我现在都快失业了!你让我活下来行吗?你以后管我姐要钱吧?”母亲在电话那端卡壳了几秒钟,“你姐最近也出去工作了,去夜场卖酒。赚的辛苦钱,没有你这么轻松。”“我不轻松。”龚强仿佛被咬了一口,“你让我攒点钱,我也想买房子,我也不想总是一个人。”母亲的回答有点莫名其妙,“你想买房子就买房子,不用和我讲的。我没钱,没法给你掏钱买房子。”
“那我不结婚了。”龚强又说。这是他的心里话。他心想,“我一个男同性恋,我结什么婚!”但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说这些。这一次,趁机吐出心里话。母亲毫不迟疑,“随你便。你不想结婚就不结婚。”顿了顿,又补上来,“这个月你先给我一千吧!”
龚强竟然开心了。他不用像别的同性恋那样需要担心结婚这个问题。🌈
彩虹赞助商
每一段认真的故事都值得珍视!